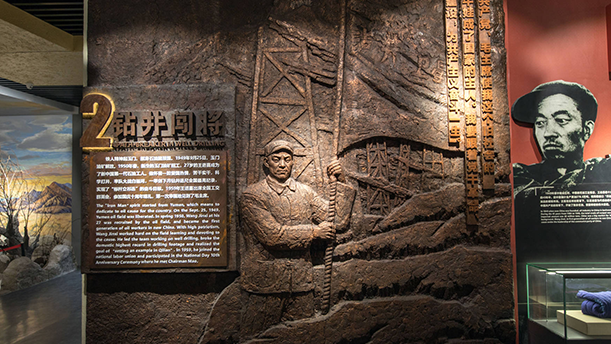和谐文化,人与自然之和谐——关于和谐社会的演讲经典篇目
 吴健溪 2025-07-30 11:30
浏览
次
吴健溪 2025-07-30 11:30
浏览
次
和谐,是人们的普遍追求。构建和维持社会和谐及人与自然之和谐,需要多方面的努力:恰当处理自然、社会的各种关系,使自然万物和一切人等各得其所,协调发展,这是自然的、物质的方面;处理好这一切,又需要有和的理念、和的道德、和的制度、和的智慧等要素,这是人文、精神的方面。此人文、精神的方面,可总称为和的文化。
早在2000多年前,中国古人就形成了“和”的宇宙观。史伯提出:“和实生物,同则不继。”《周易》说:“乾道变化,各正性命,保合太和,乃利贞。首出庶物,万国咸宁。”《中庸》说:“致中和,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。”
这几句话的中心思想为:宇宙万物因和而生,违和而灭。
由天道而知人道。天道以和为本,故一切人事,亦应以和为贵。
“礼之用,和为贵。先王之道,斯为美,小大由之”。
以和为贵,即应以求和为出发点及终极目标。不承认差别,不容纳不同的意见和利益,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,以消灭异己,压服对手为目标,必将引发动乱、战争,从而给人们带来灾难。美国以世界警察自居,推行单边主义,不断挑起战争,给世界带来动荡和灾难,乃是明证。我国曾在一个时期内强调“一个吃掉一个”,追求纯而又纯的“水晶”世界,导致“十年动乱”,亦为惨痛教训。
和如羹焉。水、火、醯、醯、盐、梅,以烹鱼肉,焯之以薪,宰夫和之,齐之以味,济其不及,以泄其过,君子食之,以平其心。君臣亦然,君所谓可,而有否焉,臣献其否,以成其可;君所谓否,而有可焉,臣献其可,以去其否。是以政平而不干,民无争心……声亦如味,一气、二体、三类、四物、五声、六律、七音、八风、九歌,以相成也;清浊、小大、短长、疾徐、哀乐、刚柔、迟速、高下、出入、周疏,以相济也。君子听之,以平其心,心平,德和……若以水济水,谁能食之?若琴瑟之专一,谁能听之?同之不可也如是。
所谓和,乃多种成分、多种因素之相成、相济,和谐共生。各个局部、各个成分各有其确定之地位和作用。每一局部和成分处于其应处之位置,各得其所,乃和谐之基础和前提。以和为目标,即须有整体观念,从整体和谐的要求看局部、个体之发展,合理地确定每一局部应处之位置,尊重其权利,协调各方面关系,做到人尽其才,物尽其用,配合协调,各得其所。只见树木,不见森林,脱离整体,孤立地追求局部、个体的发展,个体盲目的发展会破坏整体的和谐,最终会破坏整体包括个体的发展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,片面强调“征服自然”,只顾人的需要,不顾自然生态的平衡,最后导致生态被破坏,这些已成当今人类面临的头等大事。社会发展,只顾经济,不及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等方面。经济发展,单纯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,不顾其他;只顾一省一地,不顾区域和全国;只顾城市,不顾农村;只顾发达地区,不顾穷困地区……这些均由缺乏整体思维所引起的。而其后果则是导致整体之不平衡,从而阻碍整体的发展。科学发展观要求协调发展,就是以整体思维为指导,从求和出发,以和为目标,以和的理念为指导的发展观。
以上所言人与自然、国际社会、国家发展,大事如此,小至一项工程亦然。例如,对于北京国家大剧院的建筑方案,我们曾有严重的分歧和争论。分歧的焦点其实即在理念之争。中国的传统理念,求房屋建筑与周围环境之和谐;而西方建筑理念之追求,则在标新立异,独一无二。“大笨蛋”出现于天安门广场之侧,是西方建筑理念的体现。
总之,和的理念包括和实生物之宇宙观,以和为贵之价值观,使万物各得其所的全局观念,此乃和文化之第一要素。没有整体思维、全局观念,不以和为目标,就不可能有和谐。没有和谐,就不可能有发展。
贯彻落实和的理念,需要道德的支持。
社会总体的和,要求做到各个部分、个体各得其所。为保证各得其所,对于处在不同关系中、不同地位的个人,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和要求。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对立因素的和,并非单方面要求一方服从另一方,而是对双方同时提出要求,对不同方面提出不同要求。比如,父慈子孝,兄友弟恭,“为人君,止于仁;为人臣,止于敬;为人子,止于孝;为人父,止于慈;与国人交,止于信”等。每一个人必须自觉认识自己在特定地位上应尽的义务,遵守应守的道德规范,各遵其道,阴阳合德,才能达到和的目标。
和,是全局的要求;“和为贵”,就是说和的大局高于一切。总体的和谐、发展与局部、个体的发展,既统一又矛盾。个体、局部的发展是整体发展的基础、前提,同时又必须服从整体和谐的要求。为了保证总体的和谐,要各安其位,各司其职。既要安于其位,不越俎代庖,插手不该干预的事;又要尽心竭力,履行自己应尽之义务和责任。不安其位,到处伸手,要求非分的权利;或不负责任,不尽应尽的义务,这样的行径只会制造混乱,无益于和谐。各得其所和各安其位、各司其职,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。做到这一点,人人都有自己合适的位置,能发挥应有的作用,享有应得之权利,从而得到发展;又能安于其位,尽其职守,社会自然也就和而不乱了。
为了和的大局而忍辱负重,不计个人得失毁誉,是中华传统美德之重要表现,亦是实现和谐的重要保证。千古传颂的将相和的故事,是其生动的体现。蔺相如完璧归赵,受封为上卿。大将廉颇居功自傲,不服蔺相如,公开贬损蔺相如出身低贱,无功受禄,不愿与蔺相如同列,并扬言“我见相如,必辱之”。对于廉颇之所为,蔺相如并不计较,而是一再退避。相如手下因此而不满,并纷纷要求离相如而去。相如却晓以大义,说秦国之所以不敢侵犯赵国,只因为有廉颇和蔺相如两人在。“今两虎共斗,其势不俱生。吾所以为此者,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。”蔺相如的言行终于感动了廉颇,两人成了刎颈之交,共同为国效劳。这一故事清楚地说明,出于私心,争名争位,必导致不和,贻害大局;出于公心,先公后私,以大局为重,不计个人得失,才是致和的保证。 
当今现实中亦可见到,个人与集体、局部与全局、私与公的矛盾冲突,往往是阻碍、破坏和谐之主要因素。环境治理,节能减排,生态保护,最大的阻力和困难往往来自对个人或单位利益的追求,以及地方保护主义。人际关系的紧张,往往起于互不相容,责人严而责己宽,不能推己及人,严于律己,宽以待人。政党、团体、公司、单位,以至家庭内部,也常有因利益矛盾冲突而影响和破坏团结和谐之情况发生。很多人并非不知团结和谐的重要性,甚至一些人还天天高喊“和为贵”“精诚团结”,而行动中却总是将个人私利置于和谐大局之上,争权夺利,破坏和谐。
所以,仅有理论的认知仍不足以达到和谐。和谐需要道德的支持。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,各遵其道,言行有度,顾全大局,先公后私应是和谐文化的重要内容。
“和”“各得其所”之关系,需要制度和规范之保证。在古代,和的关系主要靠德和礼维持。道德为和谐之保证,前段已言及。此再言礼。礼之用,和为贵。礼之功能,即在维系社会关系之和谐。孔子言为政,曰:“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答齐景公问政,对曰: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。”均是要求以礼规范人之行为,维系社会关系之和谐稳定。颜渊问仁,孔子答曰:“‘克己复礼'‘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’。”又言孝乃“无违”“生,事之以礼;死,葬之以礼,祭之以礼”。德在礼中得到落实,由礼而得以检验;礼是德的实现形式和检验标准。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,礼对于社会和谐起了极重要的作用。中华礼仪之邦的美名亦由此而来。
礼仪规范为维系社会和谐之重要手段,它反映社会制度的要求,因而也随社会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发展变化。对于古代之礼,不宜照搬,应根据时代需要,分别对待,或淘汰,或继承,或改革。又需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,进行新礼的建设。在古代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中,公共生活不发达,人际交往限于狭小的范围。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中的诸多问题,像交通规则问题、公共卫生问题、公共场合的秩序问题,等等,古代都不存在。相应的传统道德体系中也缺乏关于公共生活的道德和礼仪。传统道德和礼仪,主要是家族伦理型的,具体说就是围绕着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长幼这五伦。这样的传统在观念上的影响就是,中国人往往伦理观念较强而公共生活的观念淡薄。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密切,公共生活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,维护公共生活秩序成为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。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,提高人们的文明素质,是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。2006年,中央文明办和国家旅游局发布了《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》和《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》,把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要求规定下来,成,为共同遵守的礼的规范。这一方面可以使道德要求落实,另一方面又可以促进人们公德意识的提高,就是以礼的形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,促进精神文明建设。
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。各种社会关系,人们的权利和义务,都要由法来规范和确定。法制乃稳定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,是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。一国之内如此,国际社会亦然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,亦须通过双边和多边的条约、共同声明等来规范。通过对话、协商、谈判而达成共识,由条约、声明等文件和一定之机制加以肯定和实施,对于构建和维持国际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作用。
总之,法制和礼的建设亦是和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和不只是一种愿望、理想,它要求实际地处理事物的矛盾,协调事物的关系,以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。这就需要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深邃、高明的智慧。人们常问,中国古代即有天人合一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、赞天地之化育的思想,却为何原来森林覆盖、水草繁茂的黄河中游生态破坏,竟成今日贫瘠干旱的黄土高原?其中原因固然很多,而科学不发达,对自然生态问题认识不足,乃其重要原因之一。面对全球气候变暖、环境污染、土地沙化、资源枯竭等问题,解决之途也有赖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应用。
水旱灾害乃人类生存发展之极大威胁。自上古鲧、禹父子始,治水即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中的大事。鲧用壅塞之法而失败,禹用疏导之法而成功。都江堰分江导流,筑堰泄洪,使四川盆地免除水灾,成天府之国。鲧非不努力,但因缺少智慧而失败,禹与后世的李冰父子则借智慧而成功。欲求人与自然之和谐,有多方面的因素,而智慧乃其中不可或缺之项。
求社会之和谐,尤须有高度智慧。20世纪50年代,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,以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之和平;20世纪80年代,邓小平提出“一国两制”,解决香港问题,都表现出高度智慧,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国内问题上,延安时期以“拥军优属”“拥政爱民”处理军政、军民关系等,都显示出智慧的光辉和力量。今天面对种种复杂问题,更需要当事者有高度智慧,以缓解矛盾、避免冲突、维护和平,共谋双赢发展。
和谐并非僵死不变。宇宙万物处于不停变动之中,和乃变动中之和,既在变中达成,也在变中维持。如何把握和处理变与和的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。在此问题上,中国古人表现出了高度的智慧。
变中求和,首先要在和中见变。《易传》云:“危者,安其位者也。亡者,保其存者也。乱者,有其治者也。”安、存、治,是和的状态;但这种状态不会永远存在,它总是要转变为危、亡和乱。因此,必须在安、存、治的时候看到危、亡、乱的危险,才能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这种变化发生。“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,存而不忘亡,治而不忘乱,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。”这就是所谓的“居安思危”。
“几者,动之微,吉之先见者也。君子见几而作,不俟终日。”事物的变化是逐渐积累起来的,积微而见著。要防止和被破坏,就要能见微知著,防微杜渐,防止剧变的发生。时刻保持忧患意识,警觉地注视变化的过程,把危险消灭在萌芽状态,这是古人一种重要的防变维和之道。
道家提出了另一种防变致和之道:柔弱处下,知足不争。《老子》云:“反者道之动,弱者道之用。”(第四十章)老子眼中的“反”,主要是“飘风不终朝,骤雨不终日”(第二十三章),“金玉满堂,莫之能守”(第九章)之类,事物从生走向死,从存走向亡,不能长久。而招致死亡的原因则是坚强:“兵强则灭,木强则折”“坚强者死之徒,柔弱者生之徒”(第九章)。因此,为避免灭亡,就应该柔弱知足,处下不争,清静无为。柔弱可以胜刚强,知足可以常足,处下可以取上,不争可以“天下莫能与之争”(第二十二章),清静无欲则天下自定,无事则可以取天下。这样,防变致和之道就归结为一个“弱”字,即“弱者道之用”。这种思想偏于消极,但也包含着合理的智慧。物极必反,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走向反面。对欲望、权力等的过分追求也会走向反面,导致灭亡。懂得这一点,约束自己,“去甚,去奢,去泰”(第二十九章),不使其过分,的确是保持个人生活正常以至国家安定的重要条件。
变,不仅有破坏和的一面,也还有化生万物的一面。《易传》说:“易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。”又说:“‘生生之谓易’‘天地之大德日生'、日新之谓盛德。”与《老子》不同,在《易传》看来,变不只是死亡和不可久,而且更重要的是变就是生,就是新事物的生生不已;只有通过变,新事物产生,才能重建和的状态;生生不已,也就能通;通了,也就能久。《老子》强调“不能久”,《易传》则以为可以而且需要通过变来求得长久。
以变求和的思想早已有之,汤武革命是这一思想的实践。《易传》说:“汤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在中国古人的思想里,并不是把变革看作绝对的坏,只一味求和而反对变革。《易传》进一步提出了“革故鼎新”的思想,说:“革,去故也。鼎,取新也。”去故才能取新,只有通过这样的变革,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。所以,《易传》又说:“‘变而通之以尽利'‘功业存乎变’。”这就充分肯定了变革对于建立功业、利在人民、利在社稷的积极意义。
上述三种主张,可以归为两种:防变维和与变以尽利。防变和用变,都是求和之道,各有其用,不可偏废。“革之时,大矣哉”时,是时机;势,是事物矛盾发展的性质、形势。对致和之道的正确选择和交替转换,取决于对时与势的正确分析和把握,取决于智慧的运用。
——钱逊
素材TV专业制作各类舞台晚会演出比赛高清LED背景大屏幕视频。
朗诵背景视频、演讲背景视频、朗诵配乐、演讲配乐、诗歌朗诵、少儿朗诵、朗诵比赛、朗诵订制。
猜你喜欢
- 搜索
-
- 同类文章